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在國家大力提倡創新與創業的今天,設計行業正在走向崛起。同時,在其發展過程中也產生了諸多問題。
柳冠中是清華美術學院責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首批文科資深教授,《設計》雜志總編,任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榮譽副會長兼專家工作委員會主任和學術委員會主任, 是中國設計學科的學術帶頭人。回首四十載,我國工業設計走過從無到有的歷程,柳教授對于當下中國設計的發展情況、設計教育,以及設計市場發展趨勢都有怎樣的理解和看法?帶著問題,《設計》雜志對柳教授進行了專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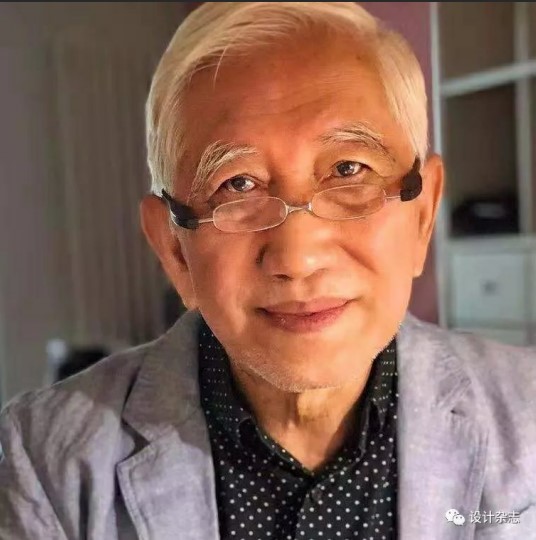
柳冠中
《設計》: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同時中國的設計市場也在崛起,請您簡單介紹40年來中國設計的一些情況。
柳冠中:中國設計從剛萌發到現在發展得很快。過去沒有“工業設計”這個概念,改革開放之后,國家引進了不少國外工業設計的思想和技術,比如提出“中國創造”這個思路。但是,這個路徑怎么走,我覺得還不是十分清楚。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設計觀念的改變基本還是以藝術設計,即一些外觀和造型的設計為主,我國的工業現狀使得人們還不可能關注設計的真正含義。我們從解放后就在引進,改革開放四十年也是在引進。結果是什么呢?就是制造的“制”是引進的,“造”是我們的,所以中國是一個制造大國。有人說大國“大而不強”,原因就在于我們主要是“造”。我目前的感覺是,凡是改革開放后引進的現在基本上仍停留在引進后的水平上徘徊。
比如現在在設計界很多企業都在做品牌,但這并不實在。品牌最重要的是“品”,而我們現在做的是“牌”,不做品。品是所蘊含的精神、歷史價值、品質和信譽,它讓一個物品變活,一個商品變高貴,一個產品變成觀念的延伸。只做表面功夫的引導我覺得遠遠不夠。
另外,在國家大工業的背景下,工業化強調標準化,設計工作需要協調需求、制造、流通、使用,以及回收等環節的矛盾。設計師恰恰是一個協調者,要兼顧各方利益。
現在很多設計師只關注概念,把真正核心東西放掉了。這40年我們開始重視設計,但對設計的認識還停留在一個最淺的層次上。政府現在已經看到這個問題了,所以需要轉型。
《設計》:轉型應該如何“轉”?重點在哪里?
柳冠中:現在有一個詞叫“痛點”,這是個商業詞,不是設計詞。想要解決問題,先要診斷為什么“痛”。馬上解決“痛點”的做法好像瞄得很準,實則只是解決了表面的問題。真正解決問題需要鉆研和研究,也就是弄清設計的本質——在生產制造之前明確為什么要生產。轉型并不是轉產,不等于說昨天做水杯,今天做手機。
工業化的轉型意味著設計要進入到生產的每一個程序,它要設計參與、干預每個程序的判斷。我們提倡設計師、設計公司一定要到“主戰場”和企業合作、參與企業產品全程序的開發。在概念層面上還要真正了解工藝、了解供應鏈、了解管理、了解整個的市場情況。這樣一來設計師的水平就提升了,設計也能發揮真正的作用。
轉型要開發和創新,而創新的根是要研究人、研究生活,這是設計的核心。日本在70年代初就提出了“設計不是滿足市場,是創造市場”。而我們現在推設計卻沒有把它放到核心位置上,還是為了商業利益,為了產值產量,為了利潤去設計的。設計師要懂得和商業合作,但要保持設計的立場,以人和社會為本。
拿品牌來說,做品牌最重要的一是質量,二是信譽,要在保證“品”的基礎上去做品牌。現在中國設計的轉型問題不能只依靠外國引進,總希望快,那樣就會一直被牽制著。習主席講的中國方案我覺得是非常具有遠見的政治智慧。
那么中國方案是什么?是我們要自力更生,實現共贏,而設計恰恰符合中國方案這個思路,那就是提倡使用,提倡服務,不提倡占有。人們的觀念需要扭轉過來。從更高的層次來說,中國戰略發展實際上是在做社會設計,設計的主戰場雖然是企業,但真正的創新是社會創新。那么,設計師就應該進行更大范圍的合作跨界,比如金融投資、社會學、規劃等領域。中國未來的希望是產業創新而不僅僅是產品創新,我覺得目前已經有這個可能性了。
《設計》: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力在不斷增強,另外各方面也在不斷發展,設計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目前中國提倡文化自信,設計上我們也需要一些自信。您覺得在設計方面應該怎樣更好地引導?
柳冠中:首先要了解文化自信是什么。我們現在的文化創意產業需要引導,一方面要做好非遺的活化,讓傳統的東西傳承下去;另一方面就是創新,“用現代的土壤來培育新品種的花朵”。也就是說,設計工作一定不能忘了主體。當下的主體是隨著整體生活水平提升,13億人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我們就要引導對“美好生活”的定義,絕非占有、炫耀,以及奢侈。
一說傳統就講到元素,一講元素就是符號,一講符號就把古代的東西搬過來,但現在時代變了,我們應該總結新的符號出來了,不能老拘泥于古代的東西。要研究現在的“土壤”,就需要設計師研究生活,研究13億人。我們要創出中國現代的東西,再過五百年又為中國豐富傳統增加了一種新的元素。而我們設計師恰恰要做這個事情,要拿設計師作品來影響大眾,影響決策者。
設計關注的是什么?不是彩虹出現。未來設計追求的是海平面是否提升,而不是浪花多么漂亮,現在大家追求的都是浪花,所以設計未來就是整體水平提升,就是合理、健康、公平,而不是奢華和炫耀。
藝術、商業關注彩虹,因為它可以賣錢,可以成名。而設計則應該關注海平面是否提升了。所以這點必然符合中國的社會方案,我們追求的不是少數的富,而是整體水平的提升。設計的責任很重,但我們對設計的認識遠遠還沒達到,總認為它是一個商業手段。所以品牌成為了下一個階段的風口,但本質不是這個。我們現在要做的最關鍵的是企業的轉型。轉型不等于抓品牌,而是抓真正的產業鏈的重組。
《設計》:近幾年越來越多的設計人開始在企業中擔任要職,您如何看待這種趨勢?這種新的位置要求設計人才具備什么樣的素質?另外中國在這方面應該有一些什么樣的引導?
柳冠中:現在有些設計公司已經開始自己辦企業了,從整個社會產業鏈的角度去開發,有很多這樣的例子成為新興的產業引導,這是個好現象,說明設計是一個產業的可能性已經出現端倪了,而不是過去的企業加上設計力量、改進產品創新,而是一個產業的創新。我覺得這是一個趨勢,但同時也應該承認我們的教育好像沒有做這樣的人才的準備。
目前我們設計教育培養人是技巧性的人才,從整個的戰略角度思考還談不到,而真正的設計教育要從國家戰略角度、從區域政治角度去培養人才的課程幾乎沒有。這就涉及到教育當中的改革,至少頂尖大學應該有這樣的人才培養,要站得高,要學會跟搞管理的、搞金融的、搞技術等人去合作,在這里面去磨合,找到共同語言。
《設計》:從一個教育者的角度來說,您認為設計教育應如何作為?
柳冠中:要培養人才,培養能夠適應未來發展的人才。再過10年20年,社會是什么樣子誰也不知道,但學校必須培養能適應未來社會的人才,而不是過了五年這個技巧不需要了,舊的知識就要被淘汰了。所以設計教育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教會他去打獵,而不是給他具體的知識和技巧。社會進步了,發展了,他到社會上自己能尋找知識,能提升自己。我的看法不見得一定正確,但我經常說“回爐”就說明大學教育在某些方面失敗了。社會在進步,未來將會有什么專業教育,什么行業,誰也不知道,那么我們就要培養具備社會適應性的人才。大學里專業課程的訓練不是目的,而作業、課程、專業的學習過程僅僅是自己擴展知識的能力的“載體”,讓學生懂得社會關系的教育才是正確的教育。知識是會過時的,那么就要培養適應新的社會的能力,能夠去吸收新的知識。“超以象外,得其圜中”,如果新一代的設計師能秉持這種信念,中國的未來會變得更加美好。
《設計》:2019年是包豪斯成立一百周年,請您談談包豪斯對中國的影響,以及針對目前中國的一些狀況,應該如何應變?
柳冠中:包豪斯的本質是從藝術跨界到技術,也就是說設計的來源、知識不僅僅是過去的東西,要“跨”。我們要繼承的是包豪斯的精神而不是形式,不能僅僅拘泥在具體的東西上。我常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嗎?”,而我們總把眼見的東西當“實”。包豪斯的設計思想是在一個新平臺上去認知設計,所以我們必須發展看,不能把包豪斯的做法直接搬過來,否則就又走錯了。

